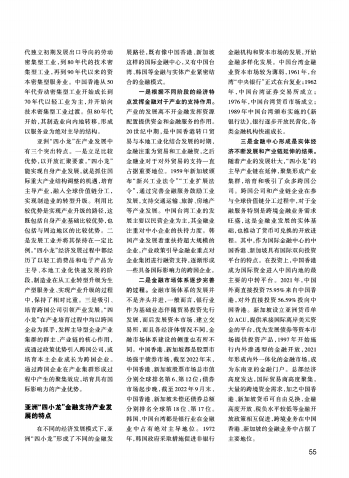文|王少辉 王方宏
作为唯一的中国特色自贸港,产业结构是海南经济发展的关键。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经历了多次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但仍存在第二产业占比偏低、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金融因素作为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外生变量,可以通过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实现调节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协同发展、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在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大背景下,具备金融开放优势的海南自贸港,可借鉴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支持的经验,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亚洲“四小龙”产业发展特点
在20世纪下半叶全球产业链转移的过程中,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抓住了发展机遇,通过发展工业有效地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促进了经济发展。
从产业结构看,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工业占GDP较高比例,特别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1960年占比分别高达28.7%、26.9%;二是在发展的前两个十年,工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大幅度提升,1960-1980年,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工业占比分别从17.3%、16.4%、28.7%、26.9%提高到32.1%、34.9%、30.9%、45.7%。从工业转型路径看,韩国从50年代的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导阶段,到60年代以重化工业为重点,再到80年代逐渐演变成以技术密集为主的产业。中国台湾与韩国发展路径近似,从50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步转向60年代面向出口的轻工业,在70年代布局重工业,到80、90年代集中力量发展技术密集型和服务业。新加坡从60年代独立初期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到80年代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再到90年代以来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国香港从50年代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成长到70年代以轻工业为主,并开始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过渡。但80年代开始,其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形成以服务业为绝对主导的结构。
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发展中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立足比较优势,以开放汇聚要素。“四小龙”能实现自身产业发展,就是抓住国际重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培育主导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利用比较优势是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这既包括自身产业基础比较优势,也包括与周边地区的比较优势。二是发展工业并将其保持在一定比例。“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以轻工消费品和电子产品为主导、本地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制造业在从工业转型升级为生产型服务业、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对比重。三是吸引、培育跨国公司引领产业发展。“四小龙”在产业培育过程中均以跨国企业为抓手,发挥主导型企业产业集群的群主、产业链的核心作用,或通过政策优势引入跨国公司,或培育本土企业成长为跨国企业。通过跨国企业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聚集效应,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优势。
亚洲“四小龙”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特点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亚洲“四小龙”形成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既有像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又有中国台湾、韩国等金融与实体产业紧密结合的金融模式。
一是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特点发挥金融对于产业的支持作用。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发挥资源配置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的作用。20世纪中期,是中国香港转口贸易与本地工业化结合发展的时期,金融注重为贸易和工业融资,之后金融业对于对外贸易的支持一直占据重要地位。1959年新加坡颁布“新兴工业法令”“工业扩展法令”,通过完善金融服务鼓励工业发展,支持交通运输、旅游、房地产等产业发展。中国台湾工业的发展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其金融业注重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韩国产业发展着重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产业政策引导金融业重点对企业集团进行融资支持,逐渐形成一些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
二是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一般而言,银行业作为基础业态伴随贸易投资先行发展,而后发展资本市场、建立交易所,而且各经济体情况不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侧重也有所不同。中国香港、新加坡都是股票市场强于债券市场,截至2022年末,中国香港、新加坡股票市场总市值分别全球排名第6、第12位;债券市场起步晚,截至2022年9月末,中国香港、新加坡未偿还债券总额分别排名全球第18位、第17位。韩国、中国台湾都是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1972年,韩国政府采取措施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开始金融多样化发展。中国台湾金融业资本市场较为薄弱,1961年,台湾“中央银行”正式在台复业;1962年,中国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1976年,中国台湾货币市场成立;1989年中国台湾颁布实施的《新银行法》,银行逐步开放民营化,各类金融机构快速成长。
三是金融中心形成是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和产业链延伸的结果。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四小龙”的主导产业链在延伸,聚集形成产业集群,培育和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和产业链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对于金融服务特别是跨境金融业务需求旺盛,这是金融业发展的实体基础,也推动了货币可兑换的开放进程。其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具有国际双向投资平台的特点。在投资上,中国香港成为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内地的最主要的中转平台。2021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75.95%来自中国香港,对外直接投资56.59%投向中国香港。新加坡设立亚洲货币单位ACU,提供承接国际离岸美元资金的平台,优先发展债券等资本市场提供投资产品,1997年开始施行内外渗透型的金融开放,2021年形成内外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成为东南亚的金融门户。总部经济高度发达,国际贸易商高度聚集,大量的跨境资金需求,加之中国香港、新加坡货币可自由兑换,金融高度开放、税负水平较低等金融开放政策相互促进,跨境业务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金融业务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四是不断适应风险管理和形势需要加强金融管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四小龙”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之后“四小龙”均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建设。中国香港持续修订金融法律,以开放性、适应性不断适应市场变化,把维护稳定的汇率作为中国香港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新加坡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准入,对银行业按照不同类别执照限制外资银行经营国内银行业务;采取与金融风险防范水平相适应的离岸金融开放政策。韩国1996年为加入OECD(简称经合组织)提前开放金融市场,导致大量外资获利后逃离,之后逐步改变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中国台湾在金融监管方面政策相对保守,但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力推动金融业重组,提升机构风险承担能力,严格金融监管指标。
海南自贸港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海南金融开放不仅要服务本地实体经济,还要充分借鉴中国香港、新加坡等金融发展经验,沿着产业链服务双循环下更大范围的实体经济,以更大程度的金融开放适当前瞻引领产业发展。通过金融开放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让资本在市场运作、市场竞争中创新产品、催生产业、引领发展。另一方面,要立足海南封关后形成的国际市场环境服务“一带一路”,以金融开放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重点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和“走出去”中资企业遇到的现实问题,包括境外融资、境外投资、人民币资金回流、规避制裁风险等。
二是自贸港金融功能要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金融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资金的交易、兑换、结算、保管、融通等功能实现资源配置的目标,自贸港金融功能的设计需要着眼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和自贸港对外开放的定位。首先,解决跨境资金流动自由问题,服务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尤其是中资跨国企业境外资金管理的安全和便利问题。其次,解决实体经济的融资问题。尤其要注重解决“一带一路”“走出去”中资企业跨境融资需求问题,通过提供跨境人民币贷款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直接融资新市场。第三,解决离岸人民币投资回流问题,形成离岸人民币投资新市场。落实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的要求,尽快落地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为央企境外资金池等各类境外市场主体提供投资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独特渠道。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打造离岸人民币新的投融资平台,破解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
三是自贸港金融功能要根据实体需求分类施策。结算、投资、交易等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针对各类金融需求的风险程度、解决措施,细分需求、分类施策,有序安排政策落地的顺序。针对不同主体分类,央企、民企、外企等主体规模和信用等级不同,其金融需求、潜在的风险等级也要有所区别。围绕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按照资金“出得去、回得来、留得住、管得了”的循环流通机制安排,针对以上不同领域、不同主体实行不同措施分类,聚焦重点主体的关键需求,以小切口突破,有针对性地予以满足,积累经验、逐步拓展、形成共识。
四是完善与高度开放相匹配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是一个强监管行业。海南金融面对的是高水平开放要求和低起点起步,金融风险防控的压力更大。应充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或地区因金融高度开放而受到较大冲击的教训,借鉴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在金融危机之后完善金融监管的做法,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的总体原则,抓紧逐条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中的金融风险防范各项政策措施,结合中国特色自贸港的金融特点和市场实际,抓住当前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契机,在政策落地中突出制度集成创新,加快构建与自贸港金融开放创新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当前,要注重研究制定海南自贸港的反洗钱指引,做好“一线放开”后的风险防范准备。H
(作者单位:王少辉,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海南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王方宏,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
本文责编/钟瑜 邮箱/ zy200928@qq.com